重读《红旗谱》:革命的初心与本心
原标题:革命的初心与本心——《红旗谱》的当代意义
我们一直忧心忡忡,当今中国正不可避免地受到理想信念失落和“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干扰。这似乎已成事实,似乎也印证了查尔斯·泰勒的忧虑,现代性的持续发展正不断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他提出的“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之命题也就显得颇为重要。但他所说的“本真理想”,显然需要置于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加以理解。就中国而言,我们不能因为进入“后革命”时代,就把革命伦理中内涵的革命初心与本心与革命一起弃之不顾。同样,我们也要认识到,这革命初心与本心所代表的“本真理想”是与共产党的领导及其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是共产党赋予其以新的内涵和蓬勃生机,认识不到这点,便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绝对主义的陷阱。今天的中国虽早已进入和平时代,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仍旧带给我们持久的感动,其对革命初心与本心的表现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感动的来源。

电影《红旗谱》海报
一
一直以来,围绕梁斌《红旗谱》的评价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肯定者从“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角度试图寻找作品中隐而不彰的丰富性和异质性,异质性的存在成了这部作品颇受肯定的重要原因。批评者则从革命现代性的必然逻辑出发否定这些异质性,进而对作品提出质疑。历史地看,不论是批评者还是肯定者,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其实都注意到了一点,即这部作品所具有的多义性特质。这种多义性,既让批评者们不安,小说中异质性的存在有损害革命的纯粹性之可能;也让肯定者忧虑,“被压抑的现代性”如果只能在革命现代性的逻辑下才能显示其价值,这样的现代性实际上并不纯粹。但也是这种多义性,让他们各取所需,他们从彼此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出发,总能从这种丰富多义性中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
应该说,这种分歧背后,体现出来的其实就是本真性命题的复杂性内涵。本真性是查尔斯·泰勒特别看重的东西,虽然在他那里,这一范畴始终语焉不详、模棱两可,但正因其界限模糊,才为他特别看重,因为一旦界限明晰,不容僭越,这一本真性也就面临着失去其再生和重新激活的可能性。
在泰勒那里,本真性命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尽管现代性带来社会的巨大发展,但也潜藏着巨大的隐忧,比如说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带来目标的丧失,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我们的生活被全面支配并助长了社会的平庸化和狭隘化等等(《现代性的隐忧》,第21-3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泰勒并没有因此否定现代性,而是从历史和现实对话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本真性这一命题:“我正在提供的图景是关于一个已经退化了的理想的图像,这个退化了的理想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实际上我想说它是现代人不可拒绝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补救性的工作,通过它,这个理想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实践”(《现代性的隐忧》,第4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这个理想即本真性命题。泰勒的思路,对我们在今天的语境重读《红旗谱》及其他革命历史小说尤其具有启发性。《红旗谱》在表现革命的逻辑时虽常常有逸出和偶然的成分在,但也正是这种逸出蕴含着朴素的本真性因素,使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这部作品时仍觉得可亲可爱,并被深深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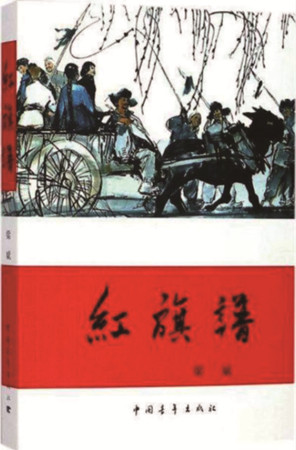
《红旗谱》
二
这种本真性的闪光,在小说伊始小虎子的目光中有极为鲜明的呈现。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可能会被研究者所忽略,但其实极具症候性,那就是小说开头小虎子的视角。小虎子是朱老忠孩童时的小名,小说中,其父朱老巩为四十八村护钟的全过程是在朱老忠彼时十几岁的目光中展现的。小说是这样开头的:“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古钟了!’”显然,这里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而且是那种宣喻式的,这里用了“狠心的恶霸”这个判断。但紧接着第二段,小说又说:“那时小虎子才十几岁,听说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而后是“走回家去”“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暴躁,小虎子扒着窗格棂儿一望”。至此,都是用的第三人主观限制视角。但很快就在不经意间变回到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朱老巩,庄稼人出身,跳哒过拳脚,轰过脚车,扛了一辈子长工!”这里视角的转移,有着多层含义。其一是表明了叙述者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对冯兰池用的是“恶霸地主”的称呼,对朱老巩用的则是带有情感色彩的感叹号。其二是表明,小虎子的视角只是插曲,小说整体上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恰恰是这插曲,显示出了本真性的辨认与传承的隐喻意义。
小虎子视角的使用当然是为了引入小说的重要人物朱老忠,但其实也带来一重疑惑,即何以要短暂地引入第三人称主观限制视角?显然,限制视角的使用,在于一种观察效用。这是通过小虎子的目光所观察到的,因而也是体认到的,和需要被命名的。通过这种凝视,小虎子朦胧而朴素地认识到他爹朱老巩何以要卫护古钟:里面有着传统意义上的打抱不平的“狭义心肠”,有着公而忘私的公心,有着为公心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这可以说就是朴素的本真性的闪光,而凝视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其辨认和传承的转换意义:小虎子正是在这种凝视的影响下慢慢长大,最终成长为共产党员朱老忠。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虽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但其实是根植于优秀传统之中的,与中国传统之间有着血脉相承的紧密关系。
通常,我们会认为革命逻辑与断裂性紧密联系在一起,革命逻辑通过否定传统和连续性而完成其现代询唤。事实并不如此。小说伊始,朱老巩大闹柳树林,而后带领妻儿被迫远走他乡。这是朱老忠返乡的前史。小说的主要部分是几十年后朱老忠带领妻儿返乡。一个是离乡,一个是返乡。小说正是在这种时空的交互关系中开始叙事的。在这当中,故乡对于朱老忠而言既是熟悉的,同时又是陌生的,因此需要重新接续和再度认同。可以说,正是这种时空关系蕴含了小说的丰富性内涵。如果说革命不仅仅是一种全新关系的建立的话,其对于朱老忠而言,还必须激起他身上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和同盟军,才能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恰恰是这种记忆和基因表明了革命的本真性内涵之存在。革命的意义正在于辨认、离析、强化和升华它。
小说中还有一个地方也多被忽略,即朱老忠与江涛兄弟之间的情感关系。小说中,朱老忠的革命本真性是在江涛兄弟革命行动的促发下被激活、强化并被认定的,这并不是简单的血缘代际遗传,而是有其超越性。即是说,本真性是一种群体认同,具有超越血缘关系的抽象性内涵。它是一种不会随着时间继替而消散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时代的感召下会重新激活并升华为革命精神和阶级感情,最后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集中彰显;因而同样,也能在民族复兴的今天重新焕发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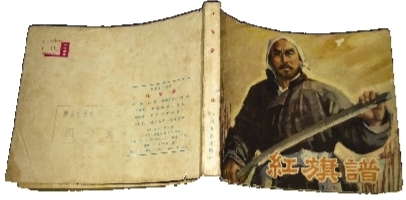
三
在对《红旗谱》的研究中,就谁是小说的主人公颇有争议。研究者大多倾向于认为朱老忠是小说的主人公。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则认为:朱老忠“更像是传统乡村秩序中一个具有侠义心肠的长者和一个革命的同路人和支持者,而不是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革命主体。”(《革命与“乡愁”》,见贺桂梅著《书写“中国气派”》,第1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这颇有点像柳青《创业史》中塑造最为成功的到底是梁三老汉还是梁生宝存在争论一样,这种争论的核心都在于革命主体的确认上。在贺桂梅看来,现代革命中,传统农民显然是不能具有革命的主体地位的。抛开争论不论,我们会发现,两部小说其实都触及了一个核心命题,即革命(某种程度上,合作化运动也是一场革命)如果不能激发传统伦理所体现的本真性,这样的革命其实是并不可亲可爱的:是现代革命激发了传统伦理,才使其成为革命本真性的。这里面,体现着一种重新发现和命名的过程。小说中,我们对朱老忠几乎所有的赞誉,可以说都与本真性有关。他豪爽、义气,他具有仁爱精神,胸怀宽广,但又朴素。他不自私,重义轻利。这是一种素朴的本真性,需要被发现和再度确认。回乡后的朱老忠,很早就朴素地认识到江涛的与众不同之处,但具体不同在哪里他并不清楚;他也清楚地看到了江涛的革命行为中所蕴含和代表着的巨大力量,这力量是他们和他们父辈的单打独斗,以及乡亲们抱团斗争所无法比拟的。江涛所代表的力量,严萍和朱老忠们一时“还不能了解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但他们能感到其中的无私、大爱和奉献精神,所以才能感动广大群众,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感动朱老忠和严萍的力量之所在,也是促使他们不断去努力思考和寻找的力量之源泉。朱老忠正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反割头税的斗争中,看到了这种力量的强大和其背后的思想资源——共产主义学说,才最终加入共产党的。
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和共产党员(江涛和贾湘农)的意义就在于,即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努力改正自己;同时也激发起他们身上蕴藏着的本真性力量,从而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员)的领导和引导,他们的反抗精神及其革命行为就只能是自发的和必定要失败的。这样看来,朱老忠入党是在正月十五灯节这一天,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它具有联结传统和现代的象征意义,本真性正是在这联结中显示出其意义和被重新激活的:这种本真性最初是在小虎子(朱老忠)的眼睛里和他的凝视中逐渐显现的,最后在朱老忠们入党时江涛的革命话语中得到确认和命名。
但我们同时也要清楚一点,本真性不是传统性。这样就能理解春兰的“革命”及其失败的原因之所在。她把“革命”二字绣在怀褂上,但她并不知道何为“革命”,因此其行径颇有点阿Q闹革命的味道。但春兰显然不同于阿Q,因为她有着变革沉闷现实的朦胧渴望,有着“迎‘新’反‘旧’”的朴素想法。“革命”二字正表达了她的这一想法。但也正因为其素朴性,所以在她与运涛的爱情关系中,他们不断遭到挫败,被春兰父亲的铁拳给硬生生拆散了。春兰有着一种对“新”的变革的渴望,这是一种发自本心的变革现实、实现幸福生活的愿望,是一种渴望爱情实现的本真性。但她不知道如何解释和阐释它,因此把“革命”二字绣在了怀褂上,而不是缝合进心里。因此不难看出,这里的本真性,不是守旧,而是求新,是与时俱进,是响应时代的召唤,是重新激活潜在的生活热情。只是,这一朴素的本真性状态,在彼时彼地,在她那里,还没有被命名,没有成形。这一命名和成形的过程,需要有革命现代性的触发和启发,需要有共产党(员)的引导和领导;春兰的“革命”行为再一次为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奠定了基础:没有共产党的出现及其领导,春兰的革命行为注定要不断走向失败。所以朱老忠们入党的时候,需要江涛给他们讲“共产党是谁们的党”和“党的铁的纪律”;这是革命得以成功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证。
在关于《红旗谱》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把《红旗谱》视为革命的起源神话写作,虽然这一研究视角有内在解构革命的嫌疑,但其实是把握住了这一小说的内核。这一革命起源,其实就是本真性的表现。这种革命起源叙事使得以下两点凸显出来。一是,革命不是凭空而来,革命建立在旧有的情感结构的基础之上。小说中朱老忠所代表的利他精神和无畏精神是这一情感结构基础。朱老忠从其父辈那里继承来,又传递给子辈——大贵们,它具有传承性,需要被不断激活和重新释放。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显示出泰勒的本真性命题的价值:挽救范畴所显示出来的正是其传承性和历史性。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革命起源于本真性,成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在这当中,是共产党及其代表着的最先进的生产力赋予这本真性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蓬勃生机。只有把“小我”和小群体、小范围的利益糅合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中去,革命才能最终走向成功。而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
本真性虽然被泰勒定义为“对我自己真实”,但“我自己”却是一个具有道德深度的存在,即是说,这是“真正的和完整的人”,“我”当中有着集体之“我们”的存在。这并不是一个原子式的自由主义个体,而是一个道德主体。它是“我们”之“同一性”的体现:“我们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的理解,是如何能够通过我们与我们所热爱的人们一起欣赏这些美好事物而转变的”,“有些善之所以为我们所理解,乃是因为此类共同欣赏才有可能”(《现代性的隐忧》,第6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红旗谱》之所以在今天的很多研究者和读者眼里,仍感到可亲可爱,乃是因为它保留了很多具有本真性的因素。这种本真性的因素,可以称其为“革命初心”或本心,即是说,既需要我们发扬光大它,也需要我们不断去激活它和重新赋予它以新的意义,只有这样,“革命初心”才能显示其永恒的魅力与活力。

账号+密码登录
手机+密码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