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典籍在西方的影响
西方对中国最初的了解,源于西人早期来华游记中或是荒诞夸张或是语焉不详的记载。真正可视为信实记载的源头,始于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书信报道和著述,他们亦是16-18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西译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所塑造的中国成为18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眼中的典范,这与19世纪欧洲文化优越视角下全然失魅的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进入20世纪,中国译者与西方汉学家共同成为典籍西译主体的新局面,既为中国文化西传赢得更多的主动权和导向性,亦带来诸多亟须反思的问题。《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下文简称《书系》)是新世纪中国学界首度系统地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域外的传播轨迹予以回顾与评判,并试图对百年来中国本土译介实践的得失以及当下中国典籍外译事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下文遂以该书所述为鉴,对中国典籍西译的历史源头、发展脉络及当下现状予以勾勒并对书系所作的思考略陈己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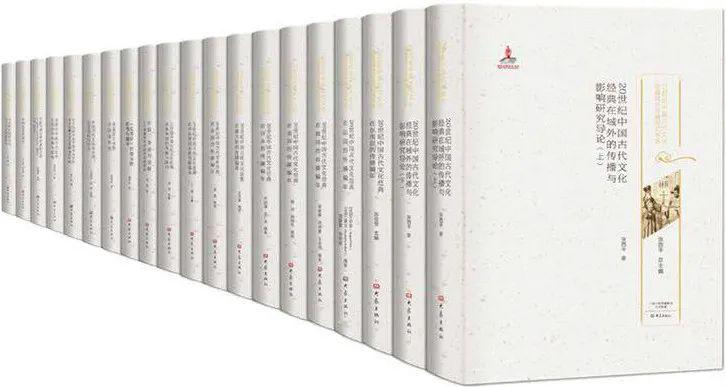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大象出版社出版
16-18世纪来华传教士的中学西传活动
16世纪到18世纪的三百年间,中国人在典籍西译的历史上是失语的缺席者。明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作为当时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主力军(以来华耶稣会士为主,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士亦参与其中),经由他们对中国典籍的译介,他们在书信、年报中对当时中国国情和社会民生的介绍以及来华各个修会围绕“中国礼仪之争”发给教廷的一系列专题论文和报告,他们塑造出一个拥有强大理性文明的中国,因其地大物博、国力雄厚、富庶优雅以及完善的政治管理制度而备受艳羡。当时的主要译介成果体现为1662-1711年间的来华耶稣会士的四个“四书”拉丁语译本:
1662年在江西建昌用中拉双语对照刻印的《中国的智慧》(Sapientiasinica),书中刊载了首部拉丁文孔子传、《大学》的全译本并节译《论语》前十章的内容。
1667、1669年,在广州、果阿合刻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是为第一个《中庸》中拉双语对照全译本。
1687年借助法王路易十四的资助,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作为对欧洲启蒙思想家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学译述,该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拉丁文译文、当时内容最为翔实的拉丁文孔子传并附孔子像、《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中华帝国及其大事纪》及中国地图等内容。该书出版后不久,随即出现多部法语、英语转译本,在当时欧洲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学者杂志》(LeJournaldesSçavans)、《博学通报》(ActaEruditorum)、《文坛新志》(Nouvellesdelarépubliquedeslettres)等学术刊物上亦涌现多篇评论性文章,充分说明了该书在欧洲的受关注程度。
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imperiilibiriclassicisex),是为“四书”拉丁文全译本首度在欧洲正式出版。
上述儒学译述的译者皆延续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合先儒、批宋儒及佛道的做法,在译作中一再声称:以利玛窦为首的来华耶稣会会士在中国经典中发现、也从中国人的口中证实,中国古人借助理性和自然法之光已经认识到真神的存在。而译作中所塑造的中国人凭借自身理性以及不懈的道德修为成功实现个人完满并获得幸福的生活模式,激发了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魁奈(FrançoisQuesnay,1694-1774)、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洛克(JohnLocke,1632-1704)、沃尔夫(ChristianWolff,1679-1754)等欧洲知识分子了解中国甚至崇尚中国“理性”文明的强烈渴望。随着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在“五经”的译介上倾力颇多,并以欧洲“中国知识代言人”的身份与启蒙思想家就中国问题保持长期通讯,欧人更为直接地获取了中国历史、地理、天文、科技、植物医药等方面的典籍译文以及关于当下社会民生的丰富信息。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正是通过与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的通讯,获其提供有关《易经》象数方面的详细介绍,促使其将《易经》与他所设想的二进制进行比较并最终确定二进制论文的发表。而他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和多封长信中的观点,亦将启蒙思想圈有关中国人究竟是无神论者抑或自然神论者的辩论推向顶峰。莱布尼茨对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寄予极大的希望,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他开篇随即指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中国。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距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正是因应启蒙思想家们对于中欧“文明之光的交换”的殷切期盼,18世纪欧洲“中国热”随即应运而生。一个因其信史的古老而撼动《圣经》的编年权威、一个无需神启仅凭个人努力和道德修为实现人生幸福的中国,正式进入欧洲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展现出其独特的世界性意义。
19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
伴随着19世纪新教传教士大量来华和欧洲专业汉学的兴起,欧人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涉猎相对18世纪而言,其译介范畴更为广泛,研究深度及其批判性观点更是令人惊叹。个中翘楚首推英国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过渡阶段的代表性人物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在其《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和《中国圣书》(TheSacredBooksofChina)的译著中,他不仅系统完成了儒家“四书五经”的英译,亦选译《道德经》《庄子》等道家经典。在完成对原始哲学宗教文献兼顾文体和文意的信实理解和翻译的同时,他撰写的那些广征博引而又细致入微的绪论及注疏、脚注中保持个人独立思考的质疑和评述,都全面展示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19世纪早期汉学家身上特有的注重实证考据的严谨学风。同样的治学路径,亦展现在法国专业汉学首席掌门人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1788-1832)及其学生儒莲(StanislasJulien,1797-1873)、鲍狄埃(Jean-Pierre-GuillaumePauthier,1801-1873)在其著述中对耶稣会士的“四书”译著的批判性借鉴以及对《道德经》《史记》等文化典籍的细致译介上。突破传教士汉学的笼罩、追求学术自觉性的特点,同样体现在这一时期汉学学术刊物对中国典籍西译的推进上,由19世纪早期的《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到19世纪后期的《中国评论》(TheChinaReview),乃至《远东杂志》(TheFarEast,IllustratedwithPhotographs)、《通报》(T’oungPao)等的创办,都呈现出对中国经典翻译数量及范围的大大增加及更为深入、中肯的学术评论。
但汉学的迅猛进步却和中国文化在当时欧洲的影响形成反比。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没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因应自身国力的增强及其对外殖民扩张,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使得原本投射向东方的崇拜目光慢慢转为鄙视,亚当·斯密、黑格尔等人均将中国视为静止、黑暗、专制的代表,尽管仍有叔本华这样的欧洲哲学反叛者为中国的自然宗教以及“天人合一”观作赞歌,19世纪俄罗斯驻北京东正教使团中的比丘林(IakinfBichurin,1777-1853)、瓦西里耶夫(VasiliiPavlovichVasilyev,1818-1900)、巴拉第(ArchimandritePalladius,1817-1878)等俄国汉学家在汉籍西译的成就上亦令人惊叹,整体上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到19世纪已被极大边缘化。但值得欣喜的是,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中国译者在此时开始正式亮相典籍西译的历史舞台,且因其学贯中西明察时势,针对一战后欧洲大众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渴望以及对西方文明没落的担忧,辜氏旨为中国文化正名而打造的一系列儒学典籍译本,出版后收获无数美誉,继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四书”译本后,二度在欧洲引发崇尚之风。
20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西方的影响
延续19世纪欧洲专业汉学打下的深厚基业,以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和顾赛芬(SeraphinCouvreur,1835-1919)为代表的汉学翻译家在20世纪上半叶依旧占据中国文化典籍西译的高地,但不同于沙畹((EdouardChavanne,1865-1918)、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所代表的法国汉学历史语文学传统,也不同于福兰阁(OttoFranke,1863-1946)、佛尔克(AlfredForke,1867-1944)等德国学院派汉学家基于民族主义视角对中国文化作出的判断,以卫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亲历者,在其译作中流露出对于东方文明的平等相待及同情性理解,卫氏的《易经》《太乙金华宗旨》译文也再度激发了黑塞(HermannHesse,1877-1962)、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等西方学者对东方“开启性真理”的高度肯定。
随着纳粹政权的上台,欧洲汉学研究的力量开始转移到美国,英文刊物《天下》的横空出世以及燕京学社的创办,标志着一批留美的中国学者有意识地主动参与到中国典籍西译的活动中。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美国专业汉学力量不断壮大并一举在20世纪下半叶实现美国中国学的兴起。尽管其研究目标由古代中国转向近当代,但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却从未停止,庞德(EzraPound,1885-1972)、安乐哲(RogerAmes)、郝大维(DavidHall)、浦安迪(AndrewPlaks)等现当代学者对中国古代诗歌、哲学典籍乃至小说的译介是为实例。其中,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模仿、对儒家典籍的学习、吸收和翻译,最终促成其“诗歌意象”理论的诞生和英美现代诗歌顶峰的到来,且终其一生,庞德都将儒学作为其精神和思想的重要支点,视为解决西方现代社会矛盾的思想源泉。而安乐哲、郝大维《论语》《中庸》译本的问世,更是在西方学术界掀起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英译新范式的激烈争论。
战后逐渐得以恢复的欧洲汉学,在保持其原有学术传统的同时,亦萌生新的发展倾向。例如与《通报》并称汉学学术期刊双雄的《华裔学志》(MonumentaSerica),在其创办初始便与中国学术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一直将中国古代经典作为翻译的重点,并开辟四裔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而其大量刊载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论文,亦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角度切实呈现了中国文化西传的早期途径,以及传教士外文汉学文献是为中国近代史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深刻认识。此外,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阿瑟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德国翻译家孔舫之(FranzKuhn,1884-1961)、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H.VanGulik,1910-1967)以及当代的霍克斯(DavidHawkes,1923-2009.)、闵福德(JohnMinford)、史华慈(RainerSchwarz)等对中国古代诗歌、古典小说、神话、笑话乃至《洗冤录》《狄仁杰案》等文化典籍流畅优美的翻译,使其成为西方社会家喻户晓的读本,成功实现了中国古代经典在欧洲社会的通俗化传播。同样备受西方读者青睐的,还有以麦家、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小说译本。麦家的小说《解密》其英译本在英美出版后,上市的第一天便打破了中国作家作品在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使其成为首位被“企鹅经典文库”(PenguinClassics)收录作品的中国当代作家,其译者英国汉学家米欧敏(OliviaMilburn)的译介贡献毋庸置疑。同样表现出色的还有该书的西班牙语译本,2014年6月当其在24个西班牙语国家上市时,首印册数达3万之多,规格已与欧美畅销书作家齐平。
20世纪后期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崛起,新时代赋予我们向世界展示自身文化丰富性的新机遇和新使命,中国典籍外译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专门从事中国文化外译与出版的机构——外文局。由其组织杨宪益夫妇等著名译者打造的“熊猫从书”(重点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英文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翻译内容上既有古代文学,亦有近当代文学,翻译体裁上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曲、杂剧、寓言、回忆录、相声、小品文等),最早担负起国家对外宣传的使命。自此,国家机构、中国学者、域外华裔学者和汉学家共同组成当代“中学西传”的多元翻译队伍,并凭借各自的资源和所长,使得中国典籍的译介无论是在类别还是数量上,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对于中国文化典籍西传的翻译研究及反思
随着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19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文化格局亦被逐渐改变,但在此过程中亦涌现出诸多的教训。譬如“熊猫丛书”在上世纪后期的销量萎缩等。外文局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国家队”,尽管其翻译活动是为国家服务并应表达国家的文化态度,但就域外传播的成效而言,关键在于如何以更为切实的方式来向不同的域外受众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对此无疑要充分借鉴传播学理论及其研究成果。这不仅要求我们的“国家队”要放下身段,致力于与对象国主流媒体及出版社合作打造其出版流通渠道,更在于要摆脱国内政治宣传的固化模式,针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不同文化圈的审美取向、文化禁忌乃至当下社会的思潮,有的放矢地选择中国文化典籍进行译介。通常一部充分考虑、尊重并回应受众群体感受的译作能有效淡化异质文化特质中的突兀感,甚至能将“他者”身上的诸多陌生特质转化为解决读者自身精神危机的思想资源,这亦是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儒学译本以及辜鸿铭译本能在不同时代的欧洲皆引发崇尚之风的原因。此外,我们亦应主动寻求与国外知名的出版集团合作——《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之所以能成为启蒙时代的畅销书,与其借助当时法国最好的出版资源有莫大关系——在其核心学术刊物或是各国文化圈的重要报刊上,定期开辟专栏,针对国外舆论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及当下热点问题等,一方面接受辩难直述己见,主动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可选译刊载与之相关的中国古代典籍、重要领导人语录文集或者外交文书,用以支持自身的观点;中国驻外大使、各国孔子学院院长定期接受当地主流媒体的采访,并向其外国受众有针对性地推荐了解中国文化的典籍读物等,这种局部、分散但在文化外宣上时效性更强的举措,可与大规模、系统性的典籍外译工程形成互补。
需要反思的另一重点是典籍外译理论的总结与创新,事实上这亦关涉中国学界期盼已久的“本土理论创新”问题。从中译外译本数目的长时段统计情况看,中国译者主体进入典籍外译史的时间短、译本数量少且出版流通渠道有限,这也悖论性地体现在长期以来在整个译介学领域具备强大学术话语权的西方翻译学理论,在“中译外”实践中的明显不适用以及本土翻译理论的缺席。《书系》导论以“译者主体研究”为线索,分析对比传教士译者与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典籍外译上的贡献及其存在的问题,指出当代中国学界既要正视传教士译介成果中存在的基督宗教及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立场,肯定其学术贡献的同时对之进行必要的学术批判,在当代需注意保持自身学术的目标、立场并跨越研究中教派、国别的局限,“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汉学研究著作中的错误”,结束对百年西学(包括西方汉学)的崇拜进入平等对话的时代,进而走出西方汉学研究的范式,怀着对自己历史文化的敬重之心,重建中国学术的叙述。
事实上,《书系》19卷本除了关注并反思中国文学典籍在西方的译介及影响,亦是国内学术界首次对中国文化、中国古代文学在南亚、东南亚、阿拉伯、东亚四个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进行集中式的研究。在其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学术于思想的影响并非只局限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实际上是以东方启蒙思想的形态,先后进入世界上多个文明体的思想体系之中,并成为其思想认识进程中的变革性因素;参与中国文化典籍译介的研究者,无论是早期的来华传教士还是当代的专业汉学家,都与中国译者和国家外宣机构共同构成中国典籍外译的历史同盟。反过来看,对于经由中国典籍外译而萌生的域外中国学研究,又对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变迁产生极大冲击,而中西文化的交错共生以及相互间的辩难启发,无疑赋予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更多的思考维度。期盼籍由对中国典籍外译史的系统梳理和经验反思,能推动学界从全球史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对外言说自身的发展理念时可用的思想资源,探寻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新可能。

账号+密码登录
手机+密码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