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我始终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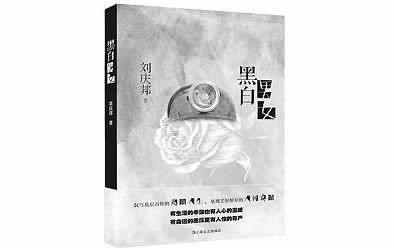
“2004年至2005年,中国煤矿先后发生三起重大事故,不到四个月,500多名工人死于矿难,而且都是青壮年。家里顶梁柱失去后,家属怎样继续生活?我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要尽快把小说写出来。”十年后,作家刘庆邦经过多次深入生活将自己长期关注的问题写成了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将视角对准四五个工亡矿工的家属,描写这些家庭事故后的生活,观察他们的现实处境。他说,家庭是“延伸意义上的矿井”,它与矿井一样都有负担,都有凶险,都有付出,都有痛苦。
煤矿是一个特殊的生态世界,矿工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群体。围绕这个题材,刘庆邦写了《神木》《哑炮》《走窑汉》《血劲》等多部中短篇小说,也陆续推出了《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三部表现矿工生活的长篇小说。为何一再写作此类题材?因为这里有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集结的是民间的烟火气息,而生与死的界限,地面与地上生活着的人的喜乐、疾苦、尊严都能在这个世界里极大展现。
“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现实”,这是刘庆邦致力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缘由所在。“生活是煤,我们只有到生活的矿井中去,才能挖出煤来。生活同时也是火,只有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才能采到火种,才能把煤点燃,使之熊熊燃烧,发光发热。”
用文学为人民服务,是一种俯下身子的行动
记者:你曾说工亡矿工家属怎样继续生活是你长期关注的话题,也是早就想写的小说,于是有了这部《黑白男女》。与以往直接对矿工、矿上生活进行描摹不同的是,你这次将视角转向了他们的家属,因为“家庭是延伸意义上的矿井”。矿井与家庭,这之间的连结有一种意味。
刘庆邦:写《黑白男女》这部小说,的确是我的一个由来已久的心愿,不写心不安,写了心才安。以前我长期在煤炭报工作,多次到现场参与煤矿事故的报道,知道每年都有不少矿工为开采煤炭献出生命。让我感到困惑和不满的是,通常衡量一场事故的损失,是以“直接”、“间接”、“经济”、“万元”等字眼作代码的,每出一次事故,都会说造成经济损失有多少多少万元。我一直不能明白,一个鲜活生命的死亡算不算在经济损失之内,如果算经济损失的话,生命是怎样换算成经济的,或者说怎样换算成万元的,换算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有关生命的科学一再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命最可宝贵,是无价的,是金钱所不能比拟和衡量的。我一直想通过一场煤矿事故,探求一下工亡事故对生命造成的痛苦,想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一个矿工的死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广泛的,而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是久远的,而不是短暂的。我想改变一下分析事故只算经济账的惯常做法,尝试着算一下生命账。换句话说,不算物质账了,算一下心灵和精神方面的账。
1996年5月21日,平顶山十矿发生了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84名矿工遇难。我立即赶到平顶山,参与了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并用心体察了那些工亡矿工家属的极度痛苦。回头我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发在《中国煤矿文艺》1997年第一期。作品发表后,很快受到煤炭部领导的重视。一位主管安全生产的副部长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感谢我从生命价值的角度,写出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并要求全国各地煤矿负责安全生产的领导同志,都要读一读这篇作品,以真正对矿工生命安全负起责任。这篇作品随后在全国煤矿所产生的积极反响是我没有想到的,一时间所有煤矿都把它作为安全生产的教育材料,几十家矿工报纷纷转载,广播站在广播,班前会在读,舞台上在演出,有的矿工的妻子还把报纸拿回家念给丈夫听。我听说,有的广播员在播送这篇作品时一再中断,泣不成声。我还听说,在班前会上读这篇作品时,不少矿工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甚至失声痛哭。一篇作品能收到如此效应,我自己也很感动,它使我对文学作品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由此我知道了,只要我们写的东西动了心,就会触动矿工的心,引起矿工兄弟的共鸣。我还认识到,用文学作品为读者服务,为矿工服务,为人民服务,不是一个说词,不是一个高调,也不是一句虚妄的话,而是一种俯下身子的行动,是一件实实在在、呕心沥血的事情,是文学工作者的价值取向,良心之功。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能不能写一部长篇小说,来描绘工亡矿工家属们的生活呢?与长篇小说相比,纪实作品总有一些局限性,而长篇小说可以想象,可以虚构,篇幅会长些,人物会多些,故事会复杂些,容量会大些,情感会丰富些,思路会开阔些,传播也会更广泛一些。有了这个想法,我心里一动,就把这个想法固定下来,成了我的一个心愿。心愿是一种持久性的准备,也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在心愿的推动下,我留心观察生活,不断积累素材,持续积累感情能量,时隔十多年后,我在2014年12月25日终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完成小说的那天是圣诞节,妻子陪我喝了一点小酒,以示庆贺!
是的,这部小说没有直接写矿难,写的是矿难发生以后的生活;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不是矿工,是矿工的家属;小说也没有写多少矿井下的场面,而是将视角转向矿工家庭。我是说过,矿工的家属是广义上的矿工,矿工的家庭是延伸意义上的矿井。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理解家庭与矿井有相似的地方,每个家庭都有压力,都有负担,都有凶险,都有付出,都有痛苦,值得我们像在井下挖掘煤炭一样,深入挖掘家庭生活的丰富矿藏。
记者:黑与白,男与女,生与死,这里有几组对立的关系。突如其来的灾难划分生与死的边界,而被留下的女人们的生活是小说要讨论的重点。你主要刻画的几个女性角色,代表了各种不同的选择,女性鲜活的个性、生活的韧性甚至生活的本质由此展现。你在小说中通过她们想要表达些什么?
刘庆邦:煤矿是一个特殊的生态世界,矿工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群体。说煤矿是特殊的生态世界,因为采煤是在几百米深的地下,见不到阳光、鲜花和飞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说矿工是特殊的生态群体,因为采矿是强体力劳动,不许女人下井,井下是单一的男性世界。越是在这样生态失衡的男性世界,女性越显得重要,越成为男性心目中的隐形支撑力量。也可以说,在井下的生死场上,每个矿工心里都站立着一个女人,女人如飘扬的旗帜,给矿工以理想和希望。然而,矿工突然倒下了,一去不返,留下了他们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矿山女人的力量才一下子突显出来,并焕发出灿烂的人性光彩。
在这部小说中,我着重塑造了五六位工亡矿工妻子的形象,她们当中有卫君梅、蒋妈妈、郑宝兰等坚强的、具有主体性的女性形象,也有王俊鸟、秦风玲、杨书琴、白煤等不够强大的、急于建立新的平衡的女性形象。她们的遭遇是共同的,都是突然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生活向她们发出了新的挑战,她们面临新的考验和新的抉择。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她们必须面向未来,建设新的生活秩序。在这些女性形象当中,卫君梅和蒋妈妈是最值得推荐的,她们坚守对丈夫的爱,对孩子的爱,并坚守自己的内心,形象堪称完美。而内心冲突最强烈、最忧伤的是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哥哥的郑宝兰,最让人心疼的是心智不健全的王俊鸟。这些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我稍一回顾,她们就向我走来,仿佛就站在我面前。我怀着对她们的敬意,小心翼翼地描绘她们的内心世界,生怕对她们造成哪怕一点点伤害。
小说是情感之物,情感之美是小说之美的核心
记者:可以看到,小说里对矿工的死亡大家持有的态度都是敬畏的,但也不畏惧谈起这场灾难,甚至对于死去矿工的纪念也带着生者更要努力活下去的坚定和勇气。我想,生与死之间的关系和意义是你所要表达的。
刘庆邦:文学作品总是要表现情与爱,生与死。死亡也是文学的主题之一。矿工和死神打交道是比较多的,生命的危机感伴随着他们,构成对生命的强烈刺激。生和死是生命的两大主题,生意味着死,到了死,才到达生命的终点。我们通常说的生命的局限,说人生是一场悲剧,也主要指死亡而言。文学表现死亡,正体现出作者积极的清醒的人生态度。人类有了自觉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才能紧紧抓住生命的缰绳,使短暂的生命更有效,更辉煌。论起对人们死亡意识的提醒,哪里也比不上采矿生活对人们的提醒更经常,更深刻。那里的提醒不光是日常的耳提面命,不光是长篇大套的行业规程,还有防不胜防的血的事实。我在河南的一座煤矿工作了九年,看到的、听到的矿工死于非命的事情不胜枚举。一次矿井下皮带着火,引起煤尘爆炸,致使九十多名矿工死亡。他们绝大多数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第二天就躺进棺材里了。我看到在矿务局总医院集中停放的棺材,棺材是白茬的,在初秋的阳光下发出刺眼的光芒。当时不让死亡矿工家属接近那些棺材,怕她们哭闹起来,局面不可收拾,一大片白花花的棺材显得有些静。可我仿佛听见,天地都为之嚎哭,矿工这种大批的、无声的死亡,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你所说的小说里所表现的人们对死亡的敬畏正是源自这里。人之所以为人,总要保留一些敬畏之心,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没有任何敬畏之心是可怕的。人们对死亡的敬畏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念,一种信仰。有了对死亡的敬畏,不仅会对逝者保持尊敬和怀念之情,还会让人善待生者,善待今生,以完善自己的生命。
记者:你的多个作品都是与矿工、矿井以及他们的家庭相关,对普通人的表现你往往是从贴近他们的角度来阐释,这从《黑白男女》的语言、叙事方式就很能感受到。你似乎更愿意将自己放置在他们当中来表达,或者说你不是持旁观者的悲悯,而是贴近人物表达他们的尊严与爱恨?
刘庆邦:我已经写了《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三部表现矿工生活的长篇小说,这三部长篇小说被评论界称为矿工三部曲。我还写了《神木》《哑炮》《走窑汉》《血劲》等更多煤矿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我写的的确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之所以一直在写平民或普通人的生活,因为我当过农民,当过矿工,本身就是一个平常人,普通人,而且我现在仍然生活在普通人中间,与普通人保持着日常性的联系。我熟悉他们的生活,能够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他们差不多等于写我自己,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还有,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关注点、兴趣点、敏感点和特定的审美对象。历史题材引不起我的兴趣,我认为那是不可想象的。官场人物也不能构成我的审美对象,只能让我心生排斥。我关注的是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感兴趣的是民间的烟火气息,对底层人的疾苦格外敏感。只有写普通人,我才会动感情,出语言,发现美,表现美。
记者:“我之所以费尽心思地要写这部小说,并不是它能挂得上什么大道理、大逻辑,也不是它能承载多少历史意义,主要的动力是来自情感。”我以为这种情感,一方面是所描绘的小说人物自身的情感,夫妻之情,父母之爱,矿工之间、家属们之间因为共同遭遇连接起来的同悲同乐,另一方面是写作者对这群人的爱与慈,悲与悯。情感为什么是动力?它是不是贯穿在小说中承载生活事实的重要载体?
刘庆邦:现在不少小说重理性,重思想,重形式,玩荒诞,玩玄虚,玩先锋,就是缺乏感情,读来不能让人感动。从本质上说,小说是情感之物,小说创作的原始动力来自情感,情感之美是小说之美的核心。我们衡量一篇小说是否动人,完美,就是看这篇小说所包含的情感是否真挚、深厚、饱满。倘若一篇小说情感是虚假的、肤浅的、苍白的,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这就要求我们,写小说一定要有感而发,以情动人,把情感作为小说的根本支撑。
当然,推动小说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多种,除了情感动力,还有思想动力、文化心理动力、逻辑动力等。只有把多种动力都调动起来,并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成就一篇完美的、常读常新的小说。
我敢说,写《黑白男女》这部长篇小说,是我十数年感情积累的一次集中爆发,几乎每天都写得我眼湿。我现在还是手写,我一边写,妻子一边用电脑打字。妻子在打稿子时,也多次被感动,一再为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发出感叹。
小说出版后,我又反复看过。不管从哪里看起,看着看着,我都会心潮涌动,不能自已。我自己如此感动,我相信读者朋友,特别是我的矿工兄弟们也会为之感动。
记者:以朴素的语言和人物行动反映生活的现实,呈现普通人的善良、乐观、坚韧、命运重压下的人性尊严,这是你小说的一个特点。这与你长期深入生活、切近现实有关,也与你抱持的对善与爱的推崇相关。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对这种现实的呈现,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通过对你作品的检索与阅读得知矿工及其家庭的生活、命运,这是一份对当下生活的记录与表达。为什么如此钟爱表达现实?或者说现实主义创作在您的作品中有着怎样的分量?
刘庆邦:尊重、维护普通人的人格和人性尊严,的确是我比较看重的小说主题。保持做人的尊严,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起码诉求。而作为底层的小人物,常常受制于人,要保持尊严是很难的,有时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人生尊严的坚守才显得弥足珍贵,才更值得尊敬。我在书中所写的那些矿工和工亡矿工家属,他们都不失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辉。
我们这一代作家赶上了国泰民安的好时候,写作时间长一些。我从1972年开始写第一篇小说,至今已写了45年,以后可能还要写若干年。长时间持续写作,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既考验我们的写作欲望和意志力,也考验我们的写作资源。怎么办?没有别的路径可走,我们只有到生活中去,不断向生活学习。为了给这部长篇小说补充素材,我到曾发生过瓦斯爆炸的河南大平煤矿定点深入生活半个月,连中秋节都是在矿上过的。生活是煤,我们只有到生活的矿井中去,才能挖出煤来。生活同时也是火,只有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才能采到火种,才能把煤点燃,使之熊熊燃烧,发光发热。
我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现实,对现实生活一直抱有兴致勃勃的热情。在创作上,我无需更多的主义,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了。我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比较宽阔,认为只要不是写人的前世,也不是写人的来世,只要写了人的今生今世,就是现实主义。前世和来世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源于一种想象。不管往前想象,还是往后想象,想象的基础还是今生,还是现实。我的想象离不开脚下的土地,离不开我的经历。加上我的小说本来就是写实的,及物的,是严格按照日常生活的逻辑推动的,怎么能脱离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经验呢!

账号+密码登录
手机+密码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